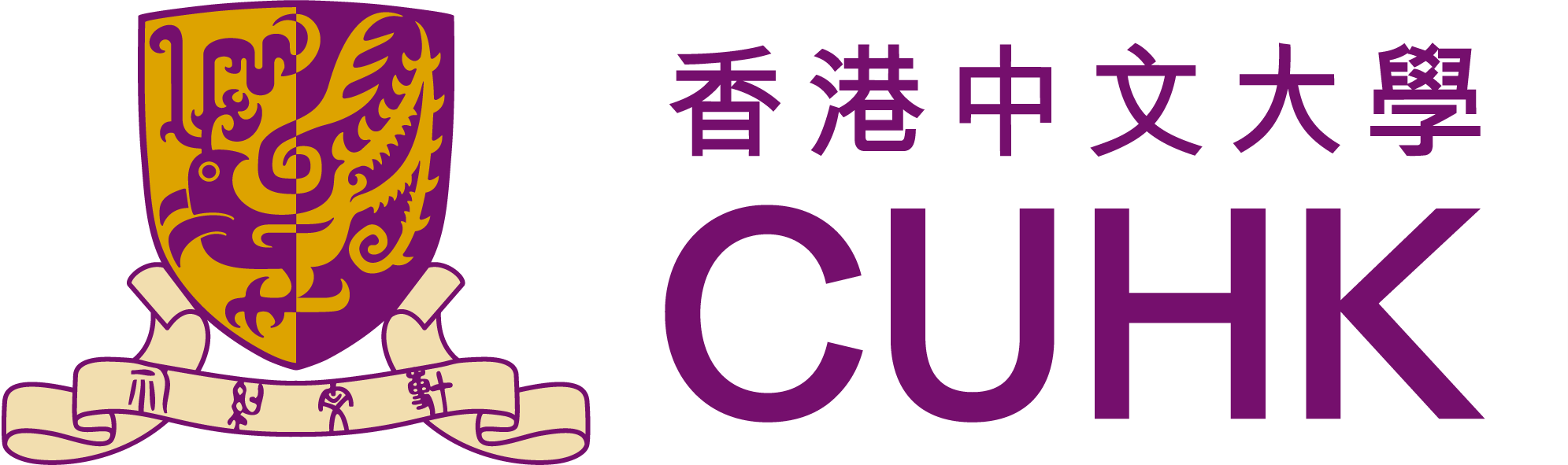中大新聞中心
中大社会工作学系发表「设立『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对香港低收入在职家庭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及生活质素的影响」研究结果「低津」鼓励工作并改善低收入人士及其家中儿童的生活质素
香港中文大学(中大)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博士联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研究助理教授张引博士于今天(9月27日)发表一项有关「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的追踪研究结果。根据数据分析显示,「低津」政策提供了一定的诱因鼓励低收入人士投入本港劳动市场。不少「低津」申请人士为达到「低津」高额津贴的申领门槛,都有策略地增加工作时数。另一方面,「低津」为贫穷人士的生活质素带来改善,增加了儿童参加课余活动和家庭进行余暇活动的机会。建议调整申请门槛及简化申请程序,以惠及更多低收入在职家庭。
为评估「低津」是否能够达到原先设想的政策效果,以及了解领取「低津」对低收入在职家庭的生活质素的影响,本研究获得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的资助,采用纵向研究设计,由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期间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数据收集。第一阶段是领取「低津」之前,而第二阶段是领取「低津」6个月之后。透过采用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法以提供多样化的数据(见附件1),比较领取「低津」(实验组)及没有领取「低津」(控制组)这两组在职家庭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及生活质素的变化。
两次电话问卷调查均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透过访问员进行访问,被访者年龄介乎18至64岁。第一阶段电话问卷调查(T1)以随机电话形式成功访问1,201名18岁或以上操粤语的香港居民,当中有453名被访者表示愿意再次接受访问,并于第二阶段的电话问卷调查(T2a)成功重访了其中247人。另外,第二阶段的电话问卷调查(T2b)亦以随机电话访问202名18岁或以上操粤语并且家庭每月总收入少于24,000元的香港居民。至于两次面谈问卷调查采取滚雪球抽样法,透过服务低收入在职家庭的非政府机构及民间团体之单位协助邀请合适的被访者。第一阶段面谈问卷调查(F1)成功访问385名年龄介乎19至63岁的人士,当中有361名表示愿意再次接受访问,并于第二阶段的面谈问卷调查(F2)成功重访了其中270人。另外,第二阶段的面谈问卷调查亦增补了210名来自已领取「低津」家庭的被访者。
研究人员进一步把来自在职家庭并有回答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问卷的被访者分为「低津」申领组(实验组)(N=190)及没有领取「低津」组(控制组)(N=327),以了解「低津」对这两组在职家庭的影响(见附件2)。在两次问卷调查中,访问员都有针对被访者家庭中工时最长的家庭成员之工作时数进行提问。纵向数据对比分析发现: 「低津」申领组最长工时的家庭成员每月工作时数达到192小时或以上的比例由T1的70.5%上升至T2的85.5%,升幅达15.0%;而每月工作时数多于144小时少于192小时的比例则减少,由T1的22.1%下降至T2的9.2%,跌幅达12.9%(见附件3)。由上述工时分段的比例可见,这些低收入人士为达到「低津」高额津贴的申领门槛,都有策略地增加工作时数,达至刚好192小时的要求。然而,这些低收入人士所从事的工种多为低时薪、低学历要求及劳动强度高的工作。工时的增加并没有提高低收入人士的工作满意度和投入感。比较T1、T2的一般工作量表(Job in General Scale)值,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见附件4)。
至于家庭生活方面,「低津」申领家庭参与休闲活动的比例有显著上升(见附件5)。在T1,有49.8% 的受访家庭表示「几乎没有参与休闲活动」,然而这一组别在T2,的比例明显下降至36.3%,减幅达13.5%。相比之下,申请「低津」家庭在领取「低津」后,「外出用膳」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观察上述两个指标在控制组于「低津」申领前后的数据,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明显变化。由此可见,「低津」促使申领家庭进行更多休闲活动,是提高生活质素的重要因素。
在家庭开支分配至不同家庭成员的比例方面,以特定金额(如1,000元或100元)作为参考提问,「低津」申领家庭在T1时投放于未成年(儿童及青少年)、青壮年(成人)和老年家庭成员的平均比例分别是: 51.9%,43.6%和31.6%;该比例在T2时变化为56.5%,47.7%和20.0%(见附件6)。由此可见,「低津」申领家庭倾向增加在未成年及青壮年家庭成员的开支,而对老年家庭成员的开销比例则相应减少。上述数据并非反映「低津」申领家庭降低了花费在长者家庭成员的绝对金额,而是反映因「低津」而获得的额外资金被分配到何处。我们估计「低津」申领家庭中长者的比例相对较少,而「低津」的申请者(多为一家之主)在获取津贴后更愿意将资源投放在子女及自己身上。相比之下,控制组并未看到类似的变化。
在生活质素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量表中三条主观幸福感问题在T1、T2的前后对比发现,「低津」申领组的被访者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对生命感到有意义两个指标并无出现明显变化。然而,「低津」申领组的被访者对生活感到快乐的程度并没有相应增强,反而出现下降的情况(见附件7)。从分组比较结果显示,被访者的「快乐感」平均分由「低津」领取前的6.13分下降至「低津」领取后的5.64分,在统计学上这是显著变化(根据配对样本t检验,p值小于0.05)。上述数据显示,「低津」申领组的被访者之快乐程度并没有跟随收入增加而上升。
在第二阶段进行的聚焦小组访问(FG),透过4间服务低收入在职家庭的非政府机构及民间团体之单位协助邀请合适的被访者,成功访问了48名来自低收入在职家庭的人士,年龄介乎19至72岁。其中27位被访者来自已成功获发「低津」的家庭,另外有21位被访者来自未有领取「低津」的低收入在职家庭。在27个已成功获发「低津」的家庭中,分别各有13个及7个家庭成功获发「低津」三次及两次,其余7个被访家庭则获发「低津」一次。在津贴金额方面,被访家庭获发的津贴金额分别由$1,500至$20,400不等。
从聚焦小组访问所得的质化数据发现,申请「低津」对申请人的工作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申请人为了符合申请「低津」的工时要求,他们不惜加班以领取高额津贴,减少了休息与子女见面的时间。然而在符合工时要求后,申请人还需为「低津」家庭入息上限而烦恼,尤其是对于从事临时工作的申请人而言,往往因此而处于矛盾之中。当达到工时及入息门槛后,申请人亦未能松一口气。有来自家庭获发多次「低津」的被访者反映申请人在每次索取工作证明时也要面对雇主不悦的面色。更坏的情况是,有从事临时工作的申请人因向雇主索取工作证明而失去工作的机会。
虽然「低津」对申请人的工作环境带来不少负面影响,然而津贴确实有助改善家庭的生活质素。「低津」让在学的儿童可以持续学习和累积更多课外知识。有被访者认为这样有助提升正在就读幼稚园或小学子女的竞争力,增加他们将来入读好学校的机会。此外,有部分被访者以「低津」为孩子购买质量较好,营养较高的食物,改善他们的健康。有家庭亦运用「低津」与子女进行余暇活动,大大改善了彼此的关系。不过,有被访者认为津贴的金额只能够补贴物价的升幅,物质生活并没有实质的改善,不足以帮助脱贫。另一方面,有部分被访者表示申请「低津」的过程涉及申报同住长者的资产和入息,不但令到长者产生疑虑,更引起家人之间的磨擦,为家庭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
综合上述纵向量化及质化研究的各项发现,「低津」在某程度上鼓励低收入人士就业及纾缓其家庭经济压力。然而,实证数据同样反映政策的推行尚有不少改善之处。为了「低津」能惠及更多低收入在职家庭,我们认为调整申请「低津」的门槛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改为只要每月工作144小时便可领取现时高额「低津」。考虑部分低收入在职家庭因要照顾家庭需要而不能长时间工作的情况,我们建议容许家中不同工作人士的工时合并计算,只要总和超过144小时便符合资格申请。至于所有单亲及有特殊照顾需要的家庭的工时规定建议减少至36小时。在计算家庭每月入息方面,我们建议改以在职家庭入息中位数为标准设上限,并以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数的50%至70%设立领取「低津」金额的递减制度,以消除现行制度中入息的悬崖效应(见附件8)。至于同住长者的收入若是由政府发放的经济援助津贴则不应计算在申请「低津」家庭的入息内。另外,我们建议同住长者的资产不应计算在申请「低津」家庭的资产限额内。在津贴金额方面,我们建议取消以工时划分的基本及高额津贴差别,改为只设家庭津贴,并根据家庭每月入息,由低于在职家庭入息中位数50%的家庭可获发全额家庭津贴$1,000(以每个家庭计)及全额儿童津贴$800(以每名儿童计)开始逐步递减金额(见附件8)。考虑到居于租住私人楼宇的儿童之居所恶劣情况,我们建议为人均居住面积少于60平方尺的儿童增加 $200特别津贴。此外,我们建议将领取儿童津贴的儿童年龄上限提高至24岁。21岁至24岁的儿童子女须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方可领取儿童津贴。最后,在申请程序方面,我们建议申请者只需于第一次申请时提供工作证明及雇主联络方法。在第二次申请起,若雇主及工作岗位没有改变,可酌情处理减免证明要求,以简化申报制度。另外,我们建议在「低津」办事处的网页中加入工时计算器的功能,协助申请人换算年假及病假的工时。
有关此研究的设计、样本、数据收集过程、第一和第二阶段数据详细分析结果及建议,请参阅印刷版的研究报告全文。